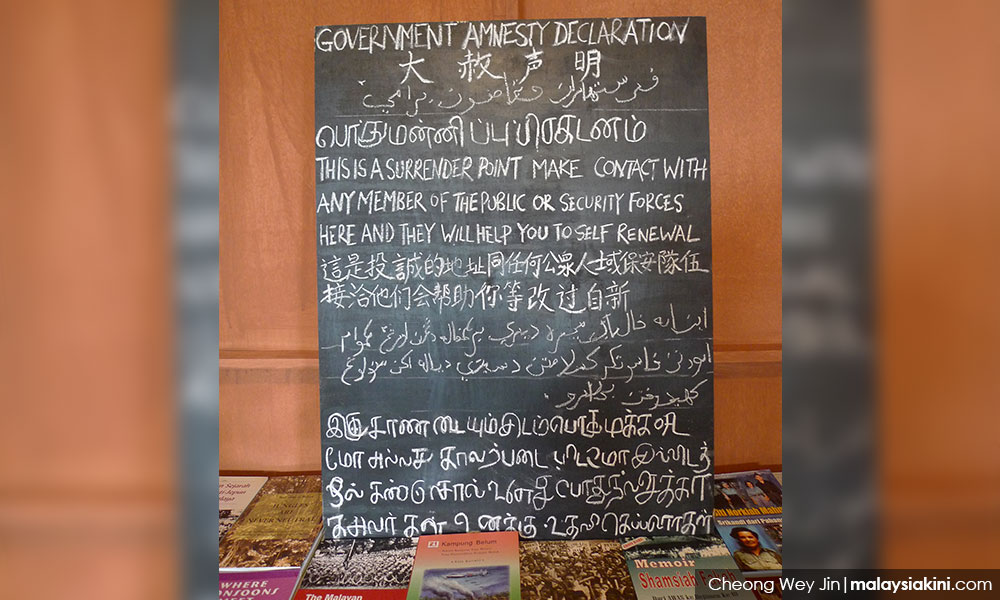今年是马来亚紧急状态70周年。
1948年6月19日,在一连串怀疑与马共有关的骚动后,英殖民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,最初从和丰开始,然后到全霹雳、柔佛,乃至整个马来半岛。英国军队和马来亚人民解放军展开游击战,一直到独立近3年后的1960年7月,紧急状态才宣告落幕,前后长达12年。
国民大学荣誉教授阿都拉曼恩蓬(Abdul Rahman Embong,见上大图)7月28日在《紧急状态与其对现代马来西亚的的影响》论坛中抛出疑问——为什么这叫紧急状态,而不是战争?
在很多人的印象里,英殖民政府宣布紧急状态是为了对付马共的暴行。可是,阿都拉曼恩蓬却点出,这其实是一场英帝国向马来亚各族群发动的战争,而人民则以反殖民与解放民族斗争反击。
他说,二战后,各殖民地掀起反殖民运动,包括越南、菲律宾、印尼等纷纷展开反殖战争,争取国家独立。
他指出,马来亚左翼早在1930年代展开反殖民运动,但为何1948年事件却被英殖民政府命名为“紧急状态”?
阿都拉曼恩蓬认为,英殖民政府命名为“紧急状态”,其实是为了掩盖英殖民资本家的庞大利益关系。
他补充,马来亚当时的橡胶和锡矿种植业,占了全经济市场各38%和58%,是英殖民政府最大的赚钱机器。而且,马来亚占有战略位置,尽管周边国家相继独立,但英殖民政府不会放过马来亚这块肥肉。
“如果命名为‘战争’,那么殖民资本家的产业,若遭受任何破损,将不会获得英国伦敦劳合社(Lloyd’s of London)保险公司的赔偿。不过,如果命名为紧急状态,保险就有得赔。”
他说,“紧急状态”之名缩小了整个历史事件,但其意义和影响却一点也不小。
“不过,在我们的记忆里,那是紧急状态。书本说是紧急状态;历史也说是紧急状态。”

残留的历史包袱
英殖民政府将其命名为“紧急状态,其实也为数代人的集体记忆定调,而阿都拉曼恩的发问,恰好提醒要从人民的角度,重新回到历史,反思命名背后的意义,以及对现今马来西亚所造成的冲击。
阿都拉曼恩蓬认为,紧急状态70年后,至今仍留下不少历史烂摊子,在当下的马来西亚持续发酵。
他说,最大的历史包袱是种族化的问题,任何事情都从种族框架理解,而把阶级问题撇在一旁不理。
以历史看今,他关切希盟新政府“应该如何形塑经济政策?是旧模式,还是新模式?新在哪里?”
其次,他指出,偏驳的历史诠释,造成历史充斥着殖民和统治精英的视角,而边缘化底层庶民的替代历史观点。
这是《马来亚紧急状态的人民历史》系列活动的首场论坛。另两名主讲人是国民大学的大马及国际研究院(IKMAS)副教授陈穆红(Helen Ting)、马来西亚华裔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启才,主持人为联办单位业余者成员苏颖欣。
本次系列的活动从7月27日至29日在隆雪华堂举行,由文运书坊、业余者、人民历史中心、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、隆雪老友联谊会、21世纪联谊会、想象马来西亚(Imagined Malaysia)、大马青年(Malaysia Muda)、对话计划(Projek Dialog)、抵抗中的学生(Students in Resistance)联合主办。

首个跨族群组织
阿都拉曼恩蓬点出,历史也低估了左翼运动在马来亚反殖民独立史,尤其是紧急状态前夕,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其中,他认为,数十个左翼组织联合而成的全马来亚联合行动委员会—人民力量中心(PUTERA-AMCJA),对马来西亚的政党组织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,可是却受到后人的低估。
他指出,PUTERA-AMCJA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史上首个跨族群的政治联盟,这些组织尽管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宗教,却能团结一致,反抗殖民,争取独立,并提出《人民宪章》(Perlembagaan Rakyat),勾勒出他们对马来亚独立后的共同愿景。
“这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套模式,从二战后开始浮现,试着团结各种族和意识形态,以争取国家独立。而英殖民政府意识到这套模式的危险,而他们应对的方式是一举铲除。”
随着英殖民政府宣布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,左翼组织纷纷遭禁,左翼领袖被捕入狱与绞刑,有者则逃离马来亚,或是加入马共,进入森林展开游击战。
他认为,从1954年的联盟、1974年的国阵,乃至如今的希望联盟,都是复制PUTERA-AMCJA当年的跨族群模式。
不过,他说,联盟和国阵都只复制了那套形式,却没有遵循这些左翼组织的精神和原则,而希盟则有待观察。
“PUTERA-AMCJA的协商方式是由下至上,以至于他们所协商的成果,是共同拥有,而不只属于精英之间,这是它重要的面向之一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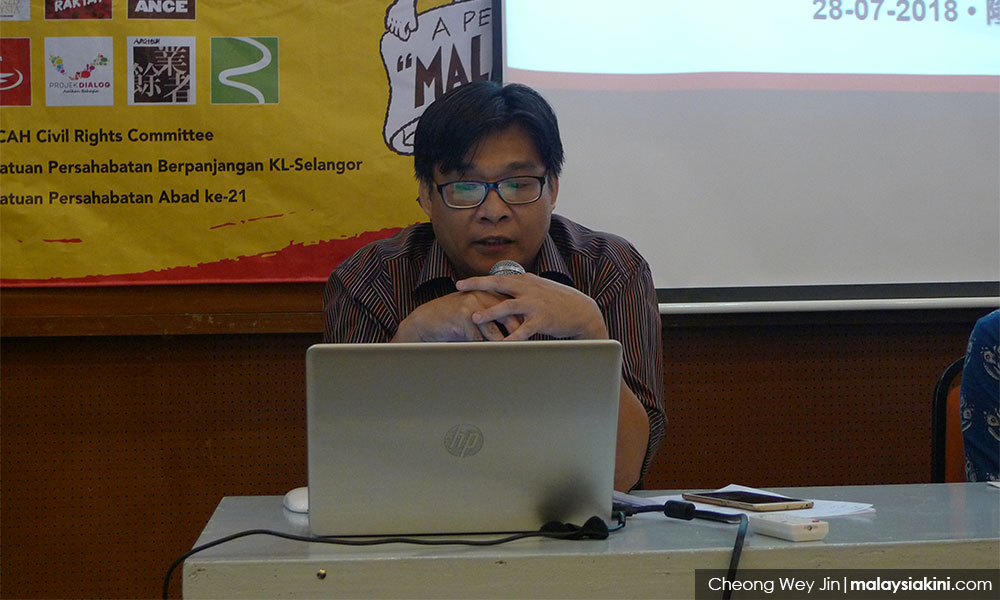
夹缝生存的华人
紧急状态迈入第二年之际,英殖民政府从原本大肆驱逐、拘留和遣返华人的剿共策略,转向实施新村计划,又称“布里格斯计划”(Briggs’ Plan)。
另一名论坛发表人何启才认为,新村计划是紧急状态的重要产物,大量华人尤其是居住森林边缘的垦殖民,被强制重置“新村”,或就地成为“新村”,四周被铁蒺藜圈围起来,与外界特别是马共隔离。
他认为,这种特定历史所塑造出来的特殊空间,直接影响了华人社会的居住形态和生活方式。
与此同时,英殖民政府推出登记政策,向新村村民登记身份。何启才说,这是英殖民政府区辨和管控华人和马共的一种手段,也间接地迫使华人开始面对身份认同和抉择的问题。
他也指出,马华公会就是在紧急状态期间诞生,并与上述两项政策紧密相关。马华成立于1949年,最初以福利组织出现,协助重置和搬迁垦殖民,同时也协助华人登记身份。
他认为,马华是英殖民政府在紧急状态的战略之一,希望有个亲英的华人组织,取代马共在华人社会的影响。后来,在紧急状态期间,马华在1952年转为政党,并与巫统和国大党参与大选,成为执政党。
另一方面,何启才也发现,紧急状态期间的华人社会可粗分为四大类,包括参与和协助当局执行剿共策略的华人;抗英的华人;被遣返回中国的华人;以及夹缝生存的华人。
其中,他说明,被遣返中国的华人虽然包括马共左翼分子或支持者,可是当中也不乏无辜被捕的华人,如商人、工人、菜农与割胶工人等。
何启才表示,根据记录,1948年至1964年,英殖民政府主要用邮轮的方式,分批将华人遣返回中国,人数高达逾5万5000人,后来中国停止接受政治难民,英殖民政府改用旅行社的方式,继续小批遣返。
他说,这些华人被迫与家人分离,后来主要留在中国各处的华侨农场,也有辗转到香港等地落地深耕,也有一些参加了中共的人民志愿军。
何启才也说,大部分华人其实是夹在英殖民和马共之间生存的华人,既不挺共,也不支持英殖民政府,处境左右为难。
他补充,华人如果支持马共,就会面临被捕或遣返的危险,但即使不表态支持,在英殖民政府的眼中,华裔几乎是马共的代名词。
然而,他指出,如果华人支持英殖民政府,则会被马共一方视为叛徒,而面临财产被掠夺甚至杀害的危险。
此外,他说,若华人不支持马共,就会受到马共对付,被抢走身份证、劳工证、米牌等。

紧缩的公民政策
值得注意的是,马来西亚是在水深火热的紧急状态期间取得独立,而紧急状态在三年后才正式宣告结束。在此前后,公民权是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的过程中,最为棘手的课题之一。即使马来亚已独立逾60年,马来西亚也已立国55年,谁是原住民,谁是外地人的问题,至今仍时有所闻。
不过,陈穆红指出,若爬梳早期英殖民统治时期的文件,公民权的问题并不如今天般紧张僵硬。
此外,她点出,中三历史课本并没有如实地反映马来亚政党团体在紧急状态期间,协商公民权课题时之复杂和困难,反而将这段历史简化为马来人为其他民族所作出的牺牲,并奠定了华裔和印裔是外来者的观点。
根据陈穆红,中三历史课本指出,“为了争取华裔支持‘精神战争’(perang saraf),邓普勒在1952年同意放宽公民权规定,好让120万名华裔和18万名印裔成为马来亚公民。放宽公民权规定显示出马来人为其他民族所做出的牺牲,以促进人民团结与和谐。”
她说,早在二战期间,凡是在海峡殖民地,或英殖民管辖的马来地区出生的人士,都可视为英国子民(British subjects)或英国保护人士(British protected persons)。
她补充,英殖民政府对公民权的定义向来宽松且一致。例如,《1867年海峡殖民地归化法令》(1867 Naturalisation Ordinance in Straits),遵照国际法的规定,公民权采属地主义(jus soli),意即凡是在该地出生的人士,都可以成为公民,而不是将其视为外来者。
她说,英殖民政府推出马来亚联邦(Malayan Union)方案时,虽然延续了一贯的精神和原则,却遭到巫统的强烈反对,最终被迫终止,之后改为推出《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条约》(1948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)。
她续说,英殖民政府跟巫统和马来王室协商后,公民政策明显紧缩。无论是《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条约》,还是紧急状态期间的《1952年国籍法》(1952 Nationality Legislation),非马来人的公民身份都受到严格规定,从此使公民权和种族课题紧紧绑在一起。
例如,《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条约》规定,本地出生的马来人能够拥有联邦公民权(federal citizen);而非马来人若要申请成为联邦公民,其双亲必须在本地出生,同时要居住满15年。
可是,她说,历史课本却告诉后人,英殖民政府给了华裔很多好处,如公民权等。
她认为,历史课本的叙述过于偏驳一方,“我们需要让学生理解争取独立的过程、复杂和难度。”